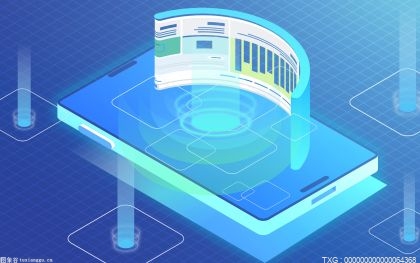(资料图)
(资料图)
陈先生的隐痛(短篇小说)
文/苏迅
吃过中饭的那一会儿,展厅里陡然松弛下来了。上午的顾客都出去找吃食,下午来的还在路上,展柜后面的人有的已经草草吃完盒饭,有的则刚送走最后一个流连在柜前的顾客也开始打开盒子,一次性筷子在青椒土豆丝或是番茄炒鸡蛋之中拨弄了几下,似乎是在这一坨之中寻找没有摘净的杂屑,或者测量着这菜的数量与温度。盒饭一般都是展会主办方“免费”提供的,说是“免费”,实则在参展费中都早已收缴了,吃的还是自己的。这些商家候鸟似的,常年参加天南海北各种古玩交流会、展销会,大多数都是老熟人了,每到一地关系密切的愿意选择紧挨在一块的展柜,这样彼此好有个照应。就像在中午这样的闲隙,其中的一位是头回来到这座城市,很想去本地同行店铺或者附近的土特产市场转转,于是就请紧挨着的那位帮忙照应展柜,自己甩开两手,一扭头出去放风了。如果在他离开的这会儿恰好有顾客光临,甚至询价,旁边的那位是会帮着开价的,到了进入买卖的实质性阶段,旁边的那位就一个电话把外面那位急急如律令宣了来。赶进来的那位右手捏住半只梅花糕,上下门牙一开一阖快速切嚼着嘴里黏甜的一团,尖起嘴唇直呼气,吐出一团团白雾,可左手上却还拎着一只黄皮纸袋,浸润了斑斑油渍,那是一种新鲜的油斑,给人透明、干净的感觉。里面,是两只滚烫的撒着红绿瓜丝的猪油梅花糕。一只是预备送给旁边的那位品尝的,另一只,或许是上次吃过谁一块糕饼或者得过一点帮助,还人情的意思。
按照以前的老规矩,行者为商,坐者为贾。这些商家有的在各自城市甚至北京、上海的古玩城开着店铺,有的则没有实体店,在全国各地参加这种展会,成了飞来飞去的“游击队”。他们在各类收藏论坛上开网店,或者网络论坛里发着帖子招揽人气兜售货品,做得有点气候的就拉起QQ群自成一家,成了势的,他的群里却也有上千个号,人马喧腾的。可是时间稍久就发现出了问题,群里的商家跟商家之间、客户跟客户之间、客户跟商家之间绕过了群主本人,直线联络上了,交流多而广了自然就会深入,很多的秘密也就不成其为秘密了,类似的“偷情”最后往往发展成“私奔”,他们各自私下加为好友,甚至又另外组了群,开辟出新的商业路线。这样的群不断分化组合,地域的界限完全被突破,人脉得到重塑,利益得到调整,既然有获利的,自然也就有失利的。反映到公开的论坛上,就有各种的吵架甚至“群殴”,很多局外人往往被他们之间的非理性和复杂性所震惊,在网络上也常常为这些势力所裹挟与压制。而这一切的背后,是市场的份额,是大小不等的利益团体,是其实已经跟真伪良莠无关的金钱与利益纠葛……这些坐在展柜后面的人,很多就是店面阔大的店主、论坛和群里的盟主,也有网络上的“键盘侠”“套中人”,既有高高在上者,也有低低在下者。此刻他们均端坐在柜台的后面,他们是平等的。是商?是贾?现在这个时代,谁还分得清呢!这些在各自的领域和层面上呼风唤雨、威风八面的人,此刻,均平淡无奇地坐在展柜的后面。睡意在上升。
在这展厅中,有几个人是看得出点与众不同的。他们用手掌掩住嘴唇、侧着脸轻声说话,男士多庄重沉稳,女士多微欣和善,开口则更是谦逊得体、娓娓道来。在这样的闲暇时光,展厅里很多人的脸上显出了懈怠神色,这懈怠一旦成型立刻就无法再掩饰住内里彻底懒散、疲沓的底色,那坐姿就七歪八扭起来,如果有足够的空间,他们可能立马顺着椅子往下躺,尽量躺平了为止。面对外界,这几个人的身上却不会暴露那样毫无节制的松懈之感,让你感觉到他们的芯子里总是有一些东西在提醒着甚至是支撑着,他们的身上总是体现出某些传统规范,也在努力维持着这个行业原有的一些自尊——没错,他们来自中国台湾。其中有两三位到北京、上海开店已有十年以上时间,现在他们也会臂肘斜撑在柜沿上,将半边脸托在掌心,发出些小小粗重的呼吸声,低沉的节拍,如同轻轻诉说着这一行的疲惫与无奈。这些悄然发生着改变的细微习惯,大概也是同步伴随着在大陆定居日久而逐步涣散,跟那些大陆同行日渐趋一的。
陈先生一年四季替换着不同面料和厚薄的手工唐装,对襟琵琶纽的式样,树脂眼镜选的是镜片窄窄而无框的那种,有时候看玉需要用电子放大镜,就把眼镜往额头上方一推,很轻巧灵便,那格式包含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港台某种时尚的元素。夏天偶尔穿一身白棉纱的无领老头汗衫,这个时候他的汗衫是必须束进长裤的裤腰里面的,否则显得邋遢不修边幅,于是便自然而然露出了皮带,以及他那枚特制的皮带头:十八开黄金包镶着一块白玉带板,浅浮雕的山水人物,山石亭子边一叶扁舟,天上半轮明月,刻着“青山水国遥”五个字的诗句,硬硬的工痕,带点桂花色的沁,明朝的古物。
陈先生跟其他人都不同——不仅跟那些松松垮垮的大陆同行显著不同,就是跟他的台湾同行也有所不同。在他看来,比他早来几年的那几位同行现在不要说为人经商,就是讲话的格调都已经跟北京、上海的商人几乎别无二致,外人甚至已经没有热情再去辨别他们到底是台湾人还是福建人了,他认为这是一种耻辱,他常常会说,这还算得上是做古董的人吗?他甚至跟新来大陆的台湾同行也不同,这些新来同行倒是有很多符合他“做古董的人”的标准,可是他觉得这还是不够的,他们应该是承担着某些特殊的文化责任的,因为在他的心里,“斯文在兹”的担当是无从推卸的。你看,近年即使是大陆的文化人都这般认同的了,于是他们就更属责无旁贷。他说,做古董,做的是文化传承。所传的是器物,其实质也是“道”。谈到这个“道”,那就说来话长……
别家的货品都是摆放在展柜中,他则在柜台上又排放了两扇黑丝绒承盘,陈列他的古玉标本,都是些残件残片,竖着一块牌子“标本非卖品”。边上另外放置高倍电子放大镜、强光电筒,他如果不说,你是猜不到在他座椅的下面,还有一架加了存储卡的单反照相机和一台手提电脑。在没有顾客的间隙,他看着手机,或是跟人手聊着古玉的话题,或是翻看着某张玉器图片。他的眼珠经常会朝头顶里面翻动,则证明他是处于研究与思索的状态,那神情使他好像已经完全超然于这庸俗的生意之外很远。当有人出现在他展柜前时,他的第一反应倒是拿着那些标本,跟人去“探讨”玉石文化的时候多,谈论生意的时候反而少些。这与众不同的做派,同行既可能见怪不怪,也可能因为过度熟悉而反生嫌隙。有时候,对面展柜里的同行可能会嘀咕几句:又来!又开讲座上课了!自然,那声音是小到对过几乎无从听见的,但是陈先生透过树脂镜片上方,是完全能够洞察同行们的一举一动,包括他们的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。做古董的人,哪个不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?不过,他是洞悉了也只当是不知不觉,说是跟客户“探讨”,实则主要是他在灌输或者传授一些鉴玉的专业知识,这不就是在进行文化传播嘛,不就是在给对方输入“保真”的心理暗示嘛,两全其美的事,何乐而不为呢?
况且这有什么呢,陈先生在台湾确实是开过讲座课的呀!陈先生跟人“探讨”到顿生投缘之感相见恨晚的时候,是经常会从座椅下面捧出他的手提电脑来,打开影视文档播放给对方看——于是二十多年之前的陈先生便在一片闪亮的雪花点中出现在镜像里,那时年轻得很,却留着时髦的英式小胡子,发型是那个时代顶流行的大波浪,眼镜也是镜片宽大的金丝镜架,这种在大陆被称为“蛤蟆眼镜”的款式就显得陈先生分外地瘦生,却更精神,跟眼前发福之后双颊饱满的这位判若两人。好在记者采访他时,电视台后期制作打上了字幕,“古玉爱好者”的头衔后面,陈先生大名赫然在目,足以令人疑窦顿消。
(节选自苏迅的短篇小说《陈先生的隐痛》)